秋意是循著風(fēng)來的。院角的老桂忽然把香息浸進(jìn)暮色里,清晨推開窗,望見遠(yuǎn)處山脊染了淡淡的金,才驚覺,又是一年秋深了。
秋陽穿過窗欞時(shí),暖意是輕勻的,細(xì)細(xì)鋪在攤開的書頁上,像極了父親書桌上那盞老臺(tái)燈的光。這樣的午后,最容易讓人沉進(jìn)舊時(shí)光里,念及父母尚在的年月,老屋的秋,每一縷風(fēng)里都裹著安穩(wěn)的氣息。
父親的書房在老屋東側(cè),朝南開著扇小窗,窗外便是母親的菜園。秋深時(shí),母親??嬷窕@,在田埂間摘野菊,說曬干了泡茶能明目。黃燦燦的花簇?cái)[在窗臺(tái)上,映得父親伏案的身影都柔和了幾分。他愛動(dòng)筆,稿紙?jiān)谧郎箱伒谬R整,鋼筆尖劃過紙面的“沙沙”聲,和著窗外風(fēng)聲、母親摘菜的輕響,成了秋日里最妥帖的音符。我總愛趴在門邊望他:看他偶爾停筆,指尖輕叩桌面,目光落在窗外老桂的金瓣上,像被陽光鍍了層暖,仿佛那桂香里,藏著寫不盡的故事。
母親的手似乎永遠(yuǎn)是干凈的,哪怕剛從菜園回來。秋涼時(shí),她總穿件棗紅罩衣,袖口洗得發(fā)白發(fā)軟,卻依舊平整。天剛亮,她就去菜園忙活:割帶露的青菜,摘架上最后一串豆角,回來時(shí)竹籃里常躺著幾顆青嫩黃瓜,用清水洗過,擺在廚房窗臺(tái),可當(dāng)果、可作菜。午后晴好,她搬竹凳坐在院中,縫補(bǔ)舊衣或擇菜,聽見父親書房飄出的鋼筆聲,便抬頭望一眼,手里針線卻不停,把秋日的靜,細(xì)細(xì)縫進(jìn)密匝匝的針腳里。
晴好的日子,父親會(huì)放下筆,背著手去城外山林。他話不多,卻會(huì)指給我看:“這是山棗,那是板栗樹”;見了落地的楓葉,便撿來夾進(jìn)隨身的書。母親不隨行,早早泡好茉莉花茶,淡甜的香裹著秋風(fēng),喝著格外清潤。下山時(shí),父親書里多了幾片楓葉,我的衣兜塞滿野果;遠(yuǎn)遠(yuǎn)望見老屋煙囪升起炊煙,就知母親在廚房候著,鍋里的蘿卜湯,正咕嘟咕嘟冒熱氣。
小城的秋是慢的。傍晚時(shí)分,鋪?zhàn)訚u次關(guān)門,只剩烤紅薯的攤子支著,甜香在涼空氣里漫開。父親愛散步,母親跟在旁,手里攥著件薄外套。路燈亮起時(shí),把兩人的影子拉得很長,時(shí)而交疊、時(shí)而隨腳步輕分,像極了那些平淡卻踏實(shí)的日子。
如今再逢秋,書房沒了鋼筆聲,廚房窗臺(tái)也沒了母親擺放的黃瓜??擅慨?dāng)秋陽落紙,或聞到烤紅薯的甜香,又覺他們從未遠(yuǎn)去:父親仍在窗邊望落葉微笑,母親仍在院中縫補(bǔ)衣裳,而我,還是那個(gè)趴在門邊,看時(shí)光在秋日里慢慢流淌、滿心歡愉的孩子。
原來那些安穩(wěn)的秋,從不是風(fēng)景的饋贈(zèng),而是父母在時(shí)的尋常。風(fēng)里的桂香、書里的落葉、灶上的熱湯,都成了歲月里,最溫潤的秋。
(國家電投江西公司羅灣電廠 陳曉)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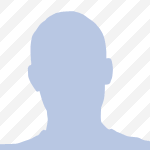






評論